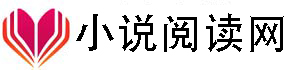16-20(7/19)
,抽得她脸颊火辣辣的疼。原来她连家里的“后”都算不上,原来形同陌路的父女关系也能这么理直气壮。
周麦琦一滴眼泪也没有,坐在输血室,伸出手臂,献了300毫升。
血液是烫的,抽进真空袋是能看见还冒着热气,滚着小小的气泡。
护士要她按压针孔,她忽然觉得恶心,喉管中有什么东西翻涌,对着垃圾桶干呕好一会儿,出现的却只有后脑勺的刺痛和太阳穴的闪烁。
爸爸每一次都说是最后一次,每一次都能装傻忘掉上一次的承诺。
他没有为她出过一分钱的学费,却不断向她索取,只因为不能绝后的荒谬言论。
再后来周麦琦独立了赚钱了交了男朋友。
半夜弟弟病发,爸爸上门哭求,用威胁性的话在门后发问:“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弟弟死吗?麦琦,周麦琦,爸爸从小就教过你,家庭才是立身之本,你想被人嘲笑吗?你想害死你弟弟吗?”
五分钟的惶恐和沉默里,周麦琦像从前的任何一次一样做出了妥协。
那一天,是蒋浮淮和她一起去的医院。
她输完血,憔悴苍白得不成样子,连独自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她叫蒋浮淮的名字,她想和他一起离开,这一方亮着灯的人间炼狱,差点要把她的骨头都吞噬。
蒋浮淮走进来牵她的手说回家。
夏天,衣衫单薄,袖口宽大,风扇动时摇摆,没按紧的、出了血的针孔以及迅速乌青的皮肤就这样曝露。
他的手臂上也留下了黄色酒精尚未风干的痕迹。
她问他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没说出话来。
周麦琦却能凭记忆推演,大一那年发入学体检单的结果,她看见过蒋浮淮的血型。
他们是一样的。
头晕目眩,眼冒金星,像喝了无数瓶假酒,吃了很多片褪黑素,也像从濒死边缘被拉了回来。
四周都是暗角,视线无法对焦。蒋浮淮的脸变得好模糊,蒋浮淮的触碰没有任何实感。
她觉得荒唐,也觉得好笑。她就快要晕过去了,她真的好难受。
甩开蒋浮淮,眼泪的频率比秒针转动还要频繁。周麦琦跌跌撞撞走到弟弟的病房,那里有好多人,护工、家属、病人,还有查床的医生。
周麦琦什么都没想,走到弟弟的床位前,忽然给了爸爸一个耳光。
*
他们不可以要求蒋浮淮付出,就算是志愿的,也不可以。
这到底算什么?
爸爸口口声声说那是蒋浮淮自己的主意,周麦琦的男朋友自愿替她分担。蒋浮淮也用他轻盈的肢体动作证明他好好的,完全没事。
可是这到底算什么?
献血是她的责任吗?是她需要无偿完成的义务吗?凭什么要蒋浮淮替她来分担。
在这个吸血鬼常驻的家里,只有她担任受害者还不够吗?一定要像增加列车乘客一样,把她好不容易收获到的一点点幸福也拉进如同《釜山行》一样的地狱吗?
周麦琦歇斯底里:“你去死!你们都去死!我没有这样的家,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灯都灭了,其他病人拉上了床帘,继母用手捂住了熟睡弟弟的耳朵,爸爸看起来还想狡辩点什么,蒋浮淮却拦腰把她抱了出去。
病房里安静了,走廊中传来大哭,片刻后,变成了小声的啜泣。
她捂着脸说对不起。
除了道歉,没有比道歉更有分量的语句。
蒋浮淮说:“你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