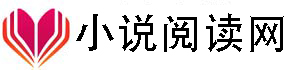16-20(6/19)
。于是要通过转移来消耗思绪。
她开始絮絮地念经,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平复心情。
环上她后背的手温暖又有力量,配合她的节奏轻轻安抚。
周裕树不知道从哪里钻出,在另一头赶来,“姐”字刚脱口,就看见昏黄灯光下相互倚靠的周麦琦和蒋浮淮。
蒋浮淮食指放在嘴边,对他比了一个“嘘”的动作。
过了很久,经念完了,周麦琦没有抬头,蒋浮淮也没有催促,直到途径的汽车摁着喇叭,吹了两声轻挑的口哨。
周麦琦猛然抬起头来。
“他走了吗?”她问的是那个在酒吧里自称是她爸的人。
蒋浮淮说:“我去赶他。”
*
手机里有很多条未接来电,全都来自没有备注的熟悉号码。
周麦琦也想过一了百了,干脆拉黑。可是血缘亲情不是那么容易断的。
她图的是家人的形式,她的家人图的是她身上流的血和她不断进账的收益。
世界上就是存在这样的规律和模式。
爸爸给她发信息,语气可怜,甚至用了整排的感叹号。
求她接电话,求她回消息,求她再见他一面,他保证,是最后一面。
保证多么廉价,上一秒信誓旦旦,下一秒可以装失忆当作经历了平行时空。
周麦琦一万次被骗,一万次不长记性。
周裕树说:“你别去,你去了我就看不起你。”
周麦琦在茶几前坐了很久,视线涣散在杂乱的书本和摊开的色彩内页中。
“周麦琦,你听到了吗?”
堂弟很少直呼她的大名,此刻精确的点名却像隔着正在运作的鼓风机,她听不清。
等到响指在眼前打过,周麦琦骤然回神。
她开始收拾茶几上的东西。空白本从一堆文字和图画书籍里被翻出,又在画笔的桶里挑出一支黑色勾线笔,周麦琦说:“我听到了。”
*
蒋浮淮忘不掉三年前和周麦琦吵的那场架。
他年轻气盛,爱付出,不爱计较,把周麦琦奉为自己的道理。
中年男性找上门来,周麦琦只请他吃了闭门羹。她对外面那个用力拍打大门,苦苦哀求的人只冷漠了五分钟。
五分钟后,她开了门,答应了中年男性的请求,跟着他去了医院。
“爸爸”的发音很简单,“爸爸”的身份似乎也很容易,“爸爸”却是周麦琦世界里遥远的人物。
她连他的名字都不想回忆,一度打过想要摘掉他们的共同姓氏的念头。
爸爸爱喝酒,爱抽烟,爱吹牛,爱在亲戚朋友面前说大话。爸爸实现不了的事情,代偿的则是周麦琦。
三岁那年,孩子连基本的意识都还没完全形成,爸爸妈妈离婚了。
周麦琦是在奶奶家长大的。
长到十八岁的时候,她离开家上大学,爸爸重组了家庭,相对来说高领的产妇为他生了个儿子。
基础条件不好的男人和女人所孕育的儿子,带着基础病出生了。
无数次的治疗需要输血,直系亲属的血液不够,爸爸就把主意打到了周麦琦身上。
她一天三份工,连营养都不达标,怎么会有多余的血给那个和她毫不相关的弟弟。
但是爸爸声泪俱下,他说他们家不能绝后。
周麦琦愣住了。爸爸在她成长阶段中的不闻不问和漠不关心忽然变成两记响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