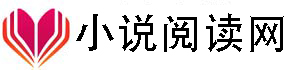30-40(8/31)
是什么时候?”“几个月,一年,三年,不超过七年。”
“幸好,”我比出一个手势,“对我来说七天就够长远了,我的脑子想不到那么远。”
克洛伊轻哧:“你就没想过再也没人来救你的话,你该何去何从吗?”
“我的每一次自杀都没期待被救。”
“因为你现在还活着,所以这么说。”
“可能吧。”
我还做不到身处安逸之中对安逸本身落井下石,考虑染料之前我更愿意先考虑我是怎样的布料。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且分秒不差,形影不离且互相伤害的人,是我自己。这个世界死亡的次数比我多得多了,也没有变好,而我每死一次,又活过来的时候,世界能杀死我的武器就少了一样。
“有一点,克洛伊,有一点是,失去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很多可能,主动丢掉的可以算失去,被抢走的可以算失去,供应商不再提供的也算一种失去,你是哪一种?”
克洛伊的眼眶一下子泛红,仿佛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能让她心碎,“你可真恶毒。”
冤枉,我想要握住她的手,但酒杯已捷足先登,我只好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失去有多少种,接纳就有多少种。”
“谁接纳?”
“我们自己。”
克洛伊像是听到什么做作的笑话,又是感到荒唐又是捧场地笑笑,“说得好高尚啊,而且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我都想呼叫911了!”
“你的确低估我了,克洛伊。”我口气严肃,“我和自己做过的斗争是你难以想象的,失败过很多次,尤其败倒在疾病面前,往后每一天都在失去我的兴趣和思考能力,和这比起来,其他失去的东西都显得微不足道起来了,都可以用‘notaskforanything’解决。”
克洛伊小声哼哼,咕哝着重复我的话:“别无所求……”随后发出质疑:“越听越像胜利者的炫
耀!牛气十足!有种你别和伊实在一起!”
太残忍了,实在是太残忍了,基因也好,人类文明也好,全都太残忍了,要一个走钢丝的初学者尝到甜头一尝就是二十几年,而不给予她认识风险的能力,以至于她摔下来的时候还在想,甜头怎么到别人身上去了。
我终于有机会握住克洛伊的手,冰块吸走了她掌心的温度,我双手捧着那只手,孵化一颗独特的蛋。
“说起来,我还活着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感受到她迟疑地要抽出手,于是握得更紧,“如果真像你之前说的那样,你救了我,为什么我们没有共度良宵?”
“什……”
“你是怕和我共度良宵之后,我会故技重施闹出人命吸引你再来陪我一晚吗?”
“你还是悠着点吧……”
“那你又为什么不能呢?非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有什么好处吗?”
“真的,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她把手抽走,再度拥抱冰块,酒杯很快见底,但她留了一口,这一口酒在后来的聊天里,很久没有消失。
不存在绝对正义的主张,多得是关锁和开锁,遇上复杂的锁可能一辈子都打不开,认命了等死,我手头上有好几把,开不了自己的锁,就把锁给别人。这是曾经一度主宰我的消极主义里,最响亮的急切。
当伊实走过来用指关节敲响桌面时,我和克洛伊正聊到她出轨的那位牙医身上,她有十分根深蒂固的把苦往酒里吐的习惯,拦也拦不住,我被迫知道了很多凯文的惊天大瓜。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伊实坐不住,前来打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