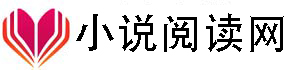40-50(20/30)
下刚举起来的手刀,对阮鸢小声道:“简单省事。”阮鸢冷静地点了点头:“懂。”
公仪襄夫人警惕地盯着阮鸢:“你想干嘛?”
阮鸢没有回答,只干脆利落地抬手朝女人后颈劈去,一声闷响,公仪襄夫人裹着被子软趴趴地倒在了床上。
池倾与阮鸢对视一眼,点头道:“不错,动作熟练了很多。”
阮鸢脸上流露出些许无奈,不好意思地道:“圣主,都是我一意孤行要来公仪家看她,才生出这么多事来。谢公子跟您都还好吧?”
“我没事。谢衡玉他……”池倾默了默,眉宇间不知染上了什么复杂的神色,看着多少有些茫然。
“他不会有事的。”她这样轻声低语,不像是回答阮鸢的问题,倒像是在安慰自己。
阮鸢觉察到不对,脸上微微显出些讶然的神情。
……看来谢公子和圣主的关系有些不寻常了。
阮鸢这样想着,还没来得及追问下去,就听池倾又道:“对了,我从前没有认真问过你去三连城之前的事,但如今倒有些好奇了。”
她伸手抚上阮鸢颊侧绯红的疤痕,轻声道:“这具身体……从始至终都是你的吗?”
阮鸢闻言微怔,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圣主呀。”
池倾歪了歪头:“你有什么事好瞒我的?”
“但此事说来话长呢。”阮鸢于是脱了鞋,将公仪襄夫人往床榻里推了推,与池倾一同盘腿坐到榻上。
她神情怔忪抱着腿,盯着床头的幕帘看了半晌,才轻声道:“圣主没有猜错,这具身子本来并不是我的,可这些年……倒也用得习惯了。习惯到让我差点忘了曾经的身份,只记得自己是阮鸢了。”
她朝池倾笑了笑:“圣主是怎么猜到,我从前用的并不是如今这具身体呢?”
池倾朝公仪襄夫人投去一个目光:“她当着我的面,喊你阿姐来着。所以只要看你们两人的长相,多少就能猜到一些了。”
因这话,阮鸢也扭头朝榻上的女人看去。那张苍白消瘦的面容下仿佛没有一点儿饱满的血肉,即便说是骨瘦如柴、形销骨立也不为过。
那过分瘦削并没有带来飘然若仙的美感,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无力的衰朽,仿佛一朵未到花期就已经凋零的花。
若是按长相来评判,公仪襄夫人如今的模样,别说是姐姐了,即便是说隔了个辈,恐怕也没人不信的。
阮鸢沉默地看着那女人很久,久到声音都略微干涩,那陌生的目光才重新染上了一丝意味不明的情愫:“圣主,躺在这里的,原该是我才对。”
故事该从哪里说起才好呢?
在阮鸢的记忆里,那约莫是南疆一个梅雨季,那年的空气比往年要更加闷热潮湿一些,以至于她身上整天都黏糊糊的,像是……抱了个暖乎乎的小孩,还得和她肉挨着肉那样的感觉。
事实上,那年的阮鸢,也确实每天都抱着一个小孩。
哦对了,那时阮鸢还不叫阮鸢。
她叫阮婷,和她的母亲……还有那个“不能管叫她妹妹”的孩子,一同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院落中。
那个小院子离南疆阮家隔了不近不远的两条街。在阮鸢更小的时候,偶尔会看见一个华服男人,挂着阮家的腰牌,在黄昏时分走进她们的小院子,目不斜视地走进母亲的屋子,然后踏着夜色匆匆离开。
阮鸢那时候并不知道,他其实就是自己的生父,她只知道他是阮家的三爷。
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在阮鸢的记忆里持续了两三年,在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