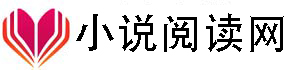70-80(22/29)
千仪恋爱时属于情窦初开,那时连牵手都能脸红很久,因此她从未往更深的方面去想。楚千仪也曾提过要做,但是岑鸣蝉没有接受,她不会,也没有想过去学,楚千仪也没有教过她。母亲在她将要前往大学时教导过她指套的使用,但是再多一些就没有讲过了。
岑鸣蝉隐隐知道要做些什么,又不是那么清楚。
就这样直到大二那年,舍友在某个深夜开了个私密的座谈会,谈到感情时,难以避免地谈到了这类话题。
岑鸣蝉作为宿舍唯一的女同,选择保持沉默。她并不想掺和进直女的讨论中,她担心有人会提到异性的使用感受,到时候她会恶心得反胃,而且她在这方面也是白纸一张,更没有什么发言权。
那晚的讨论更多的是女性如何取悦自己,这仿佛给岑鸣蝉打开了一扇大门,让她隐约窥见里面春色。
很久之后,当她尝试着去触碰时,快感是那样澎湃而汹涌,羞得她想哭。
经过几年的摸索,她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身体熟悉起来,她知道哪里是打开情欲的阀门,知道她在濒临淹没时身体的反应。
所以,她的脑海里出现的场景,是她在欺负那张白纸。
她想用唇在白纸上作画,留下鲜艳的痕迹。
要去亲吻她,吻她在颤的鸦睫,吻她柔软的唇,吻她洁白的颈,吻她滚烫的指尖。翻过身来,再去吻那漂亮的蝴蝶骨,顺着脊梁的优美弧线,以及那陷进去的腰窝。
要听她颤颤巍巍地唤姐姐,看她修长的指去抓着床单,指节因用力而变白。要听她隐忍的喘//息,再听天真又青涩的她,在灭顶的快感面前毫无抵抗之力,又不会讲一些放肆露骨的话,羞得脖颈泛红,夹着哭腔喊声不要。
岑鸣蝉在想,在那一刻,她的眼瞳里不会再有其他,只会有那个年幼的动情的自己。
她们生来亲密,是注定绞在一起的蛇。
岑鸣蝉的灵魂似乎在燃烧着,连带着皮肉的温度都在上升。
热。
但是还缺点什么。
岑鸣蝉有些焦躁,她的额上沁出一层薄汗。
想。
但就是无法抵达想要的彼岸。
就在此时,她的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是十八岁的自己打来了电话。先前冉眉冬来做客,岑鸣蝉选择把手机调成静音,之后送走眉冬,她忘记调了回来。
岑鸣蝉看着屏幕,好像抓到了什么,又什么也没有抓到,内心涌出来的羞耻感像是最后一根柴薪。
她颤抖着。
几秒过后,一切归于平静。
手机屏幕还在亮着,岑鸣蝉将手中东西关掉,接起电话。
她开口,娇软的声音里尚存着些许先前未平息的余韵:“鸣蝉。”
大概是十八岁的自己也听出来了其中的异常,她问道:“你还好吗,姐姐?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哭过。”
听到她提到哭字,岑鸣蝉觉得有些要命。
先前她幻想的画面便是对面这只楚楚可怜的小鹿,被欺负得明亮的眼睛里满是清澈晶莹的泪,要顺着泛红的眼尾滑落,要有零星一点挂在浓密的鸦睫上。
越想就越想再来一次。
岑鸣蝉自认为不是纵欲的人,如今的表现大概是生理期作祟,她只能低声叹气。
“我没事,我想去洗个澡。”
十八岁的自己此刻却俏皮地撒起娇来:“那你回来之后还爱我吗?”
有时候岑鸣蝉真的会羡慕起十八岁的自己。
她对于自己身份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