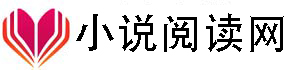60-70(15/38)
像是乐曲戛然而止,一切都来得突然。明明就在当天她们还约定好,等她们晚上各自吃完饭回来,要一起把当天比赛的视频补了。
但是现在,岑鸣蝉只能把比赛视频下载下来,独自看完。
看比赛时她总是会恍惚地想到对方,她过得还开心吗?她会想起我吗?
她也像我一样私下补完比赛吗?
岑鸣蝉痛恨自己对感情的渴求,她偷偷去看过对方的朋友圈,她想搜寻到对方痛苦的一点点痕迹。
只要她在痛苦,就证明她还爱我。
哪怕她明知道自从十八岁的自己登上职业赛场后,对方就几乎不在空间与朋友圈这种公开的地方发布动态。
时间似乎被人动过手脚,每一秒都仿佛被掰成了两秒来钟,焦灼、缓慢又漫长。
岑鸣蝉觉得自己要疯掉了。
而在这时,她接到了姑姑的电话。
“鸣蝉,明天有空吗?下班之后来家里吃顿饭吧。”
岑鸣蝉想了想,她回答道:“好,明天我早点过去。”
她没有在电话里同姑姑讲她早已离职目前一直在家写作的事。或许在明天的餐桌上,在姑姑的询问下,她才会讲出来。
面对姑姑舅舅这类的长辈,岑鸣蝉总是会心情复杂。她与长辈的关系并不算差,但也算不上特别亲近,仅有过年的时候会去走一走。
两年前那场白事,基本都是长辈出力忙前忙后,岑鸣蝉并不懂白事的规矩,只是宛如牵线木偶一般,听他人的调令。
白事过后,所有人都回归于自己的家庭。对于岑鸣蝉这个成年甚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的侄女或者外甥女,更多的也只能是含着泪叮嘱,要好好生活,为了你爸妈也得好好的。
岑鸣蝉一一点点头。
坦白讲,她不太愿意与姑姑舅舅们见面。
每次见面,长辈会透过她去怀念自己的兄弟姐妹,她坐在那里,是她,又不是她。
那一刻,她是父亲,也是母亲。
她听过了太多次这样的话,她的眉毛像父亲,她的眼睛像母亲,她结合了他们的优点。
联想起自己早死的亲人,长辈们开始讲当年岑鸣蝉的父母说过的话,做的事,讲他们如果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然后再安慰岑鸣蝉几句,要她好好生活。
到最后往往就是岑鸣蝉与长辈对坐抹眼泪,徒增感伤。
这样的相见更像是一次次自揭伤疤。虽然明知道那伤口不会痊愈,但每次揭开结痂,都是新的附加的重叠的痛苦。
她能看到那粉色的血淋淋的肉。
很疼。
没有人愿意频繁经历这样的痛苦,她宁愿窝在蜗牛壳里,触到一点点苦头就缩回壳中。
她不知道姑姑为什么会在今天打来电话喊她过去吃饭,可能是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兄长,然后想到他唯一的孩子,也或者是有话要跟她说。
只是明天只怕少不了又要再哭上一场。
她还记得,当初父母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姑姑强硬地喊她去家里过春节,岑鸣蝉实在拗不过,只能去住了几天。
她在姑姑家住得并不习惯,陌生的环境令她焦躁与不适。
最主要的是她实在接受不了与姑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些年她与姑父关系一般,仅仅是家里聚会时见过,他们常年说不上几句话。
但是共同生活之后,她就要时刻面对这位没有任何关系的异性长辈,她要避嫌。
寄人篱下的别扭与局促是